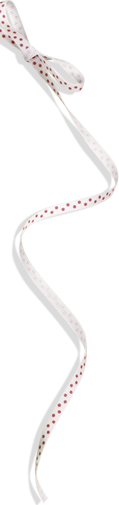
发布日期:2025-04-13 05:48 点击次数:180
#百家说史迎新春#
前言:
公元1127年的时候,女真族的大金军队骑马冲进了东京汴梁城,北宋王朝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宋朝曾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有、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这一切却在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让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汉族人,到现在都清楚记得并且心里难过的“靖康之变”。
这场悲剧发生的时候,距离大宋王朝建立已经过去了151个年头。
距离王安石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已经整整58年过去了。
距离司马光上台推翻王安石的变法,已经过了42年。大约一年半之后,王安石和司马光都离世了。
从宋哲宗亲自掌权,重新启用那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元丰党人,想让王安石的新政死灰复燃,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4年。(因为变法在宋神宗去世的元丰八年停了,所以之后支持变法的人就被叫做“元丰党人”,反对变法的人,像司马光那伙,就被叫做“元祐党人”。)

从宋徽宗重新启用那些反对变法、属于元祐党的人,并把变法新政废除,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7年。
距离那位在中国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明星,同时也是元祐党一员的苏轼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26载春秋。
管理一个大国家就像煎一条小鱼,得小心翼翼,考虑周全,不能大意。当情况变了或者环境不同了,需要做出改变时,也得慢慢来,顺着形势走,一步一步稳当地推进。
从上面这些时间变化来看,北宋朝廷的政策制度真是变来变去,一会儿一个样,像海浪一样起伏不定,政策朝令夕改,局势变幻莫测,政治风波也是层出不穷。
每次经历动荡,帝国的力量就减弱一点,直到最后无法挽回,病得很重。
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很有大家风范的政治大佬去世后,他们原本代表的两派势力,从以前的道义和政见上的不同,变成了现在为了私利、个人情绪和权力而争斗——从君子间的较量变成了小人间的争斗。
从那以后,帝国的政治就被党派的争斗拖进了泥潭,无法自拔。
苏轼离世后,一个明亮清朗的时代也随之落幕。从那以后,大宋的政治圈中,就很难再碰到那些信念执着、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了。
那是一个政治糟糕到极点、社会道德迅速下滑、好坏不分的混乱时代。
加上那位画画无人能及,但治国一塌糊涂的宋徽宗,一顿“随心所欲”加上“不负责任”的瞎搞,北宋王朝就从一座美丽富饶的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败家园。

25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从北方袭来,让北宋王朝陷入了无法挽回的绝境……
说起中国历史上那次大名鼎鼎的变法,再看看让汉族人既自豪又心酸的那段往事,大家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北宋王朝垮台的一个原因,就是像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大文豪苏轼这样的人,不支持反而阻拦了同样身为大文豪和政治家的王安石推行的强国改革,最终导致了这个结果。
还有种说法是:这都是王安石搞出来的事儿。
(一)换个说法就是:咱们先来看第一条,说得简单点儿就是……
公元1127年发生了“靖康之变”,金兵打进了北宋都城汴梁的皇宫,让藏在太庙寝宫密室里的一块石碑曝光在众人面前。
这块石碑刻着新皇帝登基时,在参拜太庙时得跪下朗读并永远守住的誓言。那个夹室,除了皇帝本人,谁也不能进去。
所以,在这之前,没人清楚石碑上写的是什么。
王夫之在《宋论》的第一卷里写道:“宋太祖刻了块石碑,放在大殿里,让以后的皇帝登基时进去跪着读。碑上写了三条规矩:一是要保护柴家的后代;二是不准杀读书人;三是不给农民加税。哎!要是做不到这三条,可真不能说他是大德之人啊。”
这是宋朝最具人性魅力的重要法令。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它是人治独裁的封建制度中,唯一由皇帝亲自颁布的,最为仁慈、伟大且明智的祖宗家训誓约。
在中国众多统一朝代里,宋朝很特别,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没有因为内部动乱而灭亡的朝代。
这也是为啥宋朝虽然地盘最小、战斗力不强,但宋太祖赵匡胤却能跟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这些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厉害皇帝相提并论的原因。

宋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和科技最为发达、辉煌的一个时代。
不过,有亮堂的地方就肯定会有黑暗的地方。
“永远不增加赋税”让老百姓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国家的钱袋子却没跟上经济的大步发展。尽管这个帝国的经济、文化和百姓生活都十分繁荣,可国家的财政收入却长期紧缺,这种情况持续了三百多年,一直伴随着整个统治时期。
五代十国时的那些武将给赵匡胤留下的印象太差,这让他特别看重文人而轻视武将,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果,宋朝成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朝代里,地盘最小、军事力量最薄弱的一个。北宋和南宋,先后都被两个游牧民族给打断进程,最终亡国。
在宋朝长达三百一十九年的历史里,打外战很少能赢。
虽说这跟“燕云十六州”一开始就没在手上有关系,但也不能说和帝国的军费开销没关系。毕竟宋朝不用老百姓服兵役,而是采用“募兵制”,这样的国防政策让财政赤字更严重了。
让已经压力山大的帝国财政更加困难的是“士兵太多”和“官员过剩”。
“冗兵”就是说国家出钱养兵。遇到灾荒时,军队还会把饥民、地痞混混收进来管着,免得他们闹事。老百姓一旦参军入了军籍,就一辈子不能变回平民了,所以军营里到处都是老的老、弱的弱、病的病、残的残。为了保证能打仗,就还得不停地招强壮的士兵进来。

帝国的正规军是禁军,地方上的军队叫厢军。在太祖的开宝年间,禁军和厢军加起来有37万人;到了太宗至道年间,这个数字涨到了66万;真宗天禧年间,已经有91万人了;仁宗庆历年间,更是达到了125万。
在不断膨胀的情况下,等到神宗皇帝即位前,数量已经涨到了140万,光军队的花费就一度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差不多是五分之六。
北宋的军队人数多,可不代表他们能打胜仗。特别是当有了太多不必要的士兵、文人管理军队的政策,还有那套古怪的军事规矩后,战斗力基本就没了,战绩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二)换种说法就是:咱们再来看看第二点,说得简单点儿就是……
宋朝的根基就是重文轻武,加上赵匡胤立下规矩,不准杀文人官员,这让宋朝的官员和读书人的日子好过到了极点,地位也非常高。
北宋的官员们,拿的薪水在历史上算是最高的了。可他们的官制挺特别,官、职、做的事情都是分开的,就是说,很多官员都不用干和他们的官位相对应的工作。
说白了,就是这个部门的官员不一定负责处理这个部门的事情。
官呢,就像是用来衡量级别和薪水高低的一个像爵位那样的等级;职呢,就只是表示一些荣誉,比如大学士、学士这些头衔;而差,才是实实在在派你去干某项工作,拥有相应的权力和要负的责任。

官职和实际工作分开后,导致很多官员有了官位和头衔,却没有具体任务可做。每年科举考试选出的新官员越来越多,没事可做的官员数量也不断增加,慢慢就变成了让朝廷财政头疼的“闲官太多”的问题。
七八成的“闲官”既有钱又没事做,人数众多。他们文化高、能花钱,还有创造时尚的好本事,这些都推动了帝国消费市场的兴旺,反而成了让经济文化达到顶峰的一个重要基础。
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最厉害的朝代,是当时所有统一的大国里GDP最高的,也是全球最有钱、最先进的国家。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做生意、国际贸易、城市建设,还是科学技术、制造手艺等等,都达到了最顶峰的状态。
那时候,已经出现了能容纳上万学生的私立大学,各种学堂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发展得非常红火。
宋朝时期,咱们中国人给全世界带去了“四大发明”里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那时候的瓷器美极了,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审美高峰。造船和建桥的技术,咱们也是遥遥领先,甩世界好几条街呢。
文学艺术这行当里,真是才华横溢,光芒万丈。
唐宋八大家里,北宋就占了六位,代表着中国古代文章的顶尖水平。那时候,无论是诗词、书法、绘画,还是塑像、建筑,审美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巅峰,真是无人能及,空前绝后。
可是,在这表面繁华的背后,国家钱包早已空空,军队也变得虚弱不堪。帝国的钱袋子长期都是花的比赚的多,到了神宗皇帝上位时,这问题已经是重得没法回头了。

除了多余的士兵、官员和平常的花钱地方,每年还得额外给辽国五十万两银子和绸缎,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银子和绸缎,说是“赏赐”。虽然这些钱只占国家收入的一点点,不到百分之二,但每当皇上觉得钱不够用的时候,想必也会因为这两笔开销感到特别丢脸。
这也是宋朝贫穷衰弱的一个明显体现。
宋神宗赵顼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他曾广泛问过大臣们的看法,想找条能让国家富裕、军队强大的路子。可遗憾的是,那些有经验的老臣们,一个个都认真地对皇帝说,要爱护百姓,多做好事、选好人来当官。他们都说要让皇帝亲近好人、远离坏人,要稳重别冲动,守住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就是没人跟他说,这日子眼看没法过了,该怎么解决;国家又穷又弱,怎么才能改变;咱们伟大的华夏民族怎样才能再次强大;要怎么做才能收回燕云十六州,让大宋帝国长久安稳、扬名立万……
德高望重的老臣富弼诚恳地建议,要是皇上能不老谈论打仗,也别太看重边疆的战功奖赏,那对国家来说真是大好事,对全天下的百姓也是大福音。
说来也巧,有一天,年轻的皇帝换上了一身帅气的军装去探望皇太后。皇太后看到赵顼这副英气逼人的样子,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但同时也提醒他:“你要是能一直都不贪图军功,那就是咱们天下老百姓的大福气了。”
春秋时期有位军事高手叫司马穰苴,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国家再大,老打仗也得完蛋;天下再太平,忘了备战也会出事儿。”从皇太后到朝廷大臣,大家都这么想,结果也好像注定了北宋58年后会遭遇大难。
柏杨学者对宋神宗赵顼赞赏有加,说在宋朝的十八个皇帝里,他算是个难得一见的、出色又聪明的君王。他披上战袍,这也透露出他既重视文化治理,又渴望军事强大,想让国家富裕、军队勇猛。
当他看到朝廷里官僚越来越多,军队庞大却战斗力不强,国家外表看似繁华,实则内里贫穷弱小,这些老臣们的治国想法和建议,让年轻的皇帝心里不免感到失望和难过。
有个人跟他想到一块去了,乐意和皇帝聊他所有想知道的事儿和想达成的目标,还信心满满地说:只要君臣俩一条心,铁了心要改革,让国家富裕强大,重现汉唐的辉煌,那根本不是啥大问题。

这个人其实就是大家熟知的王安石。
才刚刚二十岁多一点,满怀壮志的神宗皇帝,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怎么办呢?到了公元1069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二年的时候,王安石被提拔为参知政事,他挑起了大梁,全权负责推行北宋长达十七年的变法。
那时候,在宋朝的反对派里头,能跟王安石斗一斗的,也就只有司马光这么一个人了。
(三)换种说法就是:这部分讲的是,要用更简单的话来说明事情,意思还是一样的,字数也差不多。
史料上说,变法开始前,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翰林学士在神宗皇帝面前,为了变法的起因大吵了一架。他们吵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他们俩的主要不同意见。
王安石觉得国家财政变差,主要是因为缺少会管钱的人才。他说,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出一套经济改革的方法和法律法规。
司马光觉得,说到底,那些被认为擅长管理钱财的办法,其实就是变着法子给老百姓多收税。这样做不仅违背了祖宗的教诲,还会打击老百姓的创新和干劲,让国家的经济根基不稳。
王安石说:“会管钱的人,能不用多收税就让国家钱袋子满满当当。”
司马光很不赞同,他觉得世间的钱财和东西都有固定的数量。朝廷不该插手经济,想办法从百姓那里拿走一部分,或者强行掠夺,这样做比直接加税还要糟糕。
司马光始终觉得,西汉时期的桑弘羊那一套做法,其实就是跟老百姓抢利益,欺骗整个天下。王安石搞的那套变法,说白了就是照着桑弘羊的路子来的。

其实,西方世界对于经济体制里这类话题的争议一直都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论,就好比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与哈耶克主义的辩论。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主义出现了,他觉得国家稍微管一管,能补上市场的短板。可哈耶克却死活认为市场自己能管好自己,国家一插手,反而会乱套。
直到现在,全世界经济学家还在琢磨一件事: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应对各种经济危机,还有啊,在碰到特殊情况时,政府要不要出手调控,又该怎么调控呢?
两千多年前,西汉时候有个很厉害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叫桑弘羊,他就已经开始想办法让这个老牌的农业国家搞好经济,通过管控和发展工商业来让国家富裕起来,算得上是计划经济的老祖宗了。
司马迁在《史记》里对桑弘羊大加赞赏,说:“老百姓没有多交税,但国家还是很富裕。”
桑弘羊那时候推行的一项改革叫“盐铁国营”,这并非是要跟老百姓抢生意赚钱,它的意义远不止给政府多添点收入。这项政策在阻止大富豪独占重要物资、稳定物价、防止地方势力坐大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另外,在大型工业生产的合作上,因为它采用了先进、大规模且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还有技术上的不断革新,跟过去那些规模小、技术差的私营盐铁业比起来,优势简直太明显了。
不仅司马光非常痛恨桑弘羊的经济观点,其实历史上那些想要变法图强的改革者,往往都会受到守旧派和顽固书生的猛烈批评和全力打压,桑弘羊也不例外。在始元六年的二月,霍光把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和文人学者召集到京城,开了一个朝廷大会。

会议上,大家热烈讨论了要不要废除像盐、铁、酒这些由政府专营的经济规矩。贤良文学们列举了这些政策的种种不好,还指责桑弘羊这是跟老百姓抢钱,说得非常严厉。这样一来,桑弘羊就提出了让人深思的“三个问题”。
1,国家运行得花大钱,光靠农民交的税哪够啊,要是不实行这些制度,国家的钱袋子从哪儿鼓起来呢?
2,要是碰到战争、天灾这些急事儿,国库没钱了怎么办?
3,要是中央在钱财等好多方面没法完全压住地方,那以后地方势力要是变大了,管不住了,出现了像古代藩镇那样各自为政或者起兵叛乱的情况,那可怎么是好呢?”
变法改革没有哪种方案能确保到处都适用,十全十美。一项全面的改革,也难免会在某些地方出现一些不好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部分问题就一股脑儿地全部否定。
王安石变法的那些具体做法,很多都是从西汉时期的桑弘羊那里借鉴来的经济策略。
宋朝那会儿,老百姓生活得还算富裕,但前提是得国家稳定、长久和平。说到底,国家经济好了,百姓生活才会好;国家强大了,百姓才能真正富裕。光靠忍耐和受气,是换不来长久稳定的。假如司马光能预知58年后发生的“靖康之变”,他还会批评汉武帝因为过度用兵导致百姓生活困苦吗?
不过,司马光这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他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和王安石在财政、金融这些经济学领域相差甚远。但要说到对千百年来帝国政治社会怎么运作,还有对各个朝代兴衰更替的深刻理解与敏锐眼光,司马光则是王安石难以比拟的。
如果他们俩能真心实意地一起合作,那肯定能补上漏洞,互相成就。但事情已成定局,没法重来,这两位政治领袖的关系越来越差,最后变成了死对头,帝国的领导层也因此彻底分成了两派。这样一来,宋帝国就慢慢地变得不稳定,越来越动荡不安了……
(四)换种说法就是:咱们再来看看第四点,说得简单点儿就是……
神宗皇帝最后拍板,决定站在王安石那边,支持他的改革想法。因为国家钱包越来越瘪,快要走不动了,不改不行,变法已经是火烧眉毛的事儿了。
再者,王安石那一套有头有尾的变法理论,其中有些已经得到了证实,对这位年轻的皇上来说,非常有说服力。
在那次有名的辩论里,王安石的看法从道理上讲是对的。其实不用加税也能让国家钱袋子鼓起来,这样的方法有很多,早就被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给证实过了。
比如说,让钱转得更快,把生产环境搞好来多生产东西,这些都是这样的做法。其实,王安石搞的“青苗法”就是这样一个挺妙的办法。这个法子在他当县令那会儿就试着用过,老百姓特别买账。试过之后觉得不错,就在他的地盘上大面积推广开了,成绩还挺亮眼。

那时候,帝国的乡下借高利贷的风气很盛,这是导致农民破产和土地被富人吞并的主要原因,对帝国的伤害非常大。
所以,到了庄稼还没成熟,家里缺钱的时候,政府就会借钱给农民,只收半年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这可比当时的高利贷便宜多了,只有它的五分之一)。这样既能帮农民搞好农业生产,又能给政府多赚点钱,真是个大好事,一举两得。
这个“青苗法”,还有像成立三司条例司、推行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以及收取免行钱、实施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都是用金融手段来治理国家的办法,它们在当时的世界上,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数一数二的。
历史学家黄仁宇感叹说:“没想到在九百多年前,王安石就已经通过信用贷款来促进经济发展了。他的想法跟现在的经济观念挺接近,但跟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差别可大了。”
按照台湾作家柏杨的说法:“王安石就像那个时代的超人一样。”
他的经济头脑远超司马光,非常先进。但这也有好有坏,带来了一些不好的结果。后来有人感慨:天还没亮呢,王安石就起得太早了!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是因为他准确理解和把握了帝国的历史走向。
他特别赞赏那种让百姓安宁、政府不多干预的“文景之治”,并且下定决心要像圣人那样,用德行和努力创造一个和谐平静的社会。从他写的那本有名的《资治通鉴》里,能看出他觉得汉武帝和桑弘羊通过国家掌控生意,走上了跟百姓抢利益的路子。

王安石直接采用了桑弘羊的“均输法”作为他的变法措施之一,连名字都没变,完全是照搬过来的。
均输法就是说,各个郡国给朝廷的贡品,不用直接送,而是先按当地的价格换算成当地的特产,交给均输管理部门。然后,均输官会把这些特产运到其他地方去卖,因为那里稀缺,所以可以卖高价。这样做能统一调配各地的土特产,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太多,让物资分配更合理。朝廷这样既不用花钱就能得到各种物资,还能通过买卖赚取很多利润。
桑弘羊实施的这个办法才一年时间,山东地区的漕运量就从汉初的几十万石一下子涨到了六百万石;国家的应急粮仓和边境的粮库都被装得满满的,丝绸布帛的数量也比汉初多了五百万匹。
王安石变法里的市易法,其实就是桑弘羊说过的平准法。这个办法就是国家建个专门管东西价格和买卖的机构,通过买卖市场上的货物,在价格高时卖出,价格低时买进,来达到稳定价格的目的,并且还能帮国家多赚点钱。
这些话不仅体现了两千多年前适时实施计划经济的长处,也有点像现代金融运作的方式。不过,这样一来,就让一些商人赚不到钱,民间的经济活力也很快就下降了。
另外,还推行了“算缗”和“告缗”这两项制度。算缗呢,就是对商人收财产税。告缗则是鼓励大家举报那些不报税或者少报税的商人,一旦查实,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这下子,“告缗”的事情到处都是。
被举报的人,不光所有财产会被收走,还得去边疆服兵役一年。这种规矩虽然帮政府搜刮了民间大堆的钱财,但也害得好多中等收入的家庭破了产。而且,它还让人心变坏,这让一直提倡做好事、看重品德的司马光非常痛恨。
(五)换句话说就是,这一部分的内容讲的是,咱们得换个简单易懂的说法来说明这事儿,但意思还是一样的,字数也差不多。
司马光多次跟神宗皇帝提起汉朝初期“萧何定下的规矩曹参继续沿用”的那个有名故事。

司马光说“管理大国就像煎小鱼”,从制定政策到实施,都得特别小心、谨慎行事。政策得围着百姓转,不能今天一变明天一变,国家的政治架子也不能轻易摇晃。
汉朝刚开始的时候,曹参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他觉得最难管的其实不是老百姓,而是那些当官的。他认为,只要能让官员们安分守己,别老去打扰百姓,让他们好好干自己的活儿,别瞎折腾,这样官员们能安心工作,老百姓也能快乐生活,咱们华夏民族就能不断地创造出财富,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
这也是司马光成为坚决反对派头头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一个大国家要搞个大改革,那难度和挑战可大了去了,这时候,各行各业的人才就显得特别重要。结果后来发现,在改革推进的时候,因为像司马光这样的大官不支持,王安石就急匆匆地用了一批没咋经历过风雨、也没怎么考验过能力和品德的新人,结果导致改革的一些关键地方走了样,没控制好。
更关键的是,这些新加入的力量,在政治斗争的激烈场上,要是稍有不慎,就很容易从急着想成功变成耍小聪明,再进一步就是什么都不顾了,最后落到被人看不起的地步。

真可惜啊,那些支持并继承王安石变法的人,像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邓绾他们,最后都臭名远扬,大多数还被写进了历史书里的奸臣名单里。
司马光凭借他对历史和帝国制度独到的见解,加上对过往朝代官员管理的深刻理解,用看透人心的眼光,准确预料到变法中会因人为因素带来灾难性的坏结果。
但当帝国财政碰到大麻烦,非得改革不可的时候,司马光就显得有点缺乏远见。毕竟汉朝初年跟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不能老一套办法不变,缺少灵活应变和决断力,而且他的治国想法也太理想化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品行高尚,文采斐然,官声也好,而且在各个领域都有着令人惊叹的才华和出色的治国能力。在坚守自己的政治观点上,他们俩都像普通人难以做到的那样,有着极其相似的倔强和坚持。
王安石心里一直琢磨着要改革。他出了名以后,好几次都没要朝廷给他的大官职位,非要到地方上去当个县令这样的小官不可,还说他要等皇上哪天想改革了,才肯做大官。
神宗皇帝铁了心要支持王安石搞变法,司马光呢,就去了西京洛阳,一门心思写他的《资治通鉴》。皇上本想让他当个枢密院副使,算是帝国军事上的二把手,可司马光给拒绝了,他直接跟皇上说,只要变法不改,他就不接受朝廷的高官厚禄。
两位政治大佬在同一朝廷共事,他们的政治信仰、原则和人品德行都让人敬佩不已,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截然相反,真让人感慨万千啊。

其实他们俩之间没啥私人过节,反倒是都挺欣赏和喜欢对方的。
在王安石还没成为朝廷大官之前,司马光跟大家想法一样,觉得比他小两岁的王安石,行事特别,不随波逐流,肯定藏着了不起的本事和好品质。
他说起王安石,真是让人大吃一惊:“介甫特别有才华,学问也大,志向高远得很。要是不挑大梁也就罢了,但只要他担起重任,好日子就快来了,老百姓都能沾他的光。”
司马光站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后,用他自己的办法,接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让他再好好想想自己的政治想法和治国办法。王安石回了封信,就是那篇很有名的、中学课本里都学过的《答司马谏议书》。打那以后,他俩的友情就完全断了,各走各的路了。
北宋王朝最大的倒霉事就是两个人变成了政治上的死对头。这一来,整个国家的士大夫们就明明白白地分成了两拨,一开始还只是为理念、为道义争来争去,慢慢地就变成了争权夺利。
权力之争愈演愈烈,政治氛围很快变差,政治上的道德底线也不断被突破。两股政治势力慢慢丢掉了理性和道德的束缚,结果让整个帝国的官场都分不清好坏对错了。
最后,整个北宋就像被一股坏风气包围了,变成了一场场野兽般的争斗,你刚下场我就上,互相撕咬不停。就这样,在一轮又一轮的混乱更替中,北宋大步迈向了黑暗的深渊……
(六)换种说法就是,这部分内容讲的是,咱们要把事儿说得更简单明了些,意思还是一样,字数也别差太多。
王安石推行的改革,他的好心和想要达到的目的,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

随着改革措施的进行,国家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过了十几年,等到宋徽宗赵佶当上皇帝时,宰相蔡京对他说:现在国库里头还有五千万缗钱,钱多得是,足够让朝廷的排场再大上一些。
接着,品味独特又爱玩的艺术家赵佶开始玩起了各种新花样,和他身边那群史上最大规模的奸臣团伙一起,把祸害国家和百姓的能耐用到了头,直到整个国家都快撑不住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国库变得满满当当,这个变法的主要目的算是达到了。不过,因为选错了人帮忙,变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大问题,就像灾难一样,导致老百姓的积极性大减,国家经济也短暂地陷入了不景气。
另外,几乎所有的老臣、重臣,还有那些最有声望的文化人士,都变成了变法的坚决反对者,这使得国家管理层完全分裂,党争日益激烈,政治情况变得前所未有的糟糕和腐败。
从公元1069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二年的二月份起,一直到公元1085年,宋神宗元丰八年的三月份,神宗皇帝驾崩时结束,这十七年时间里,王安石在皇上的支持下推行了“熙宁变法”,过程充满了波折。
新登基的哲宗小皇帝才9岁大,因此国家大事由一直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代为管理。到了五月,司马光被召回京城,全权负责国家事务,他毫不犹豫地废除了实行了十七年的变法新政,而且谁劝都不听。这次大转变在历史上被称为“元祐更化”。
有个细节挺值得注意:苏轼以前强烈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变法,但他却建议司马光不要一刀切,留下那些已经被证实对国家和百姓都有好处的新政策。不过,司马光果断拒绝了苏轼的提议。

苏轼他们感慨地说:“哎,怎么又碰上个倔脾气首相……”。就是说,怎么又来了个跟王安石一样固执己见的首相呢!
苏轼被这种不讲道理的政治思维搅得心里很乱,他越来越觉得高尚的品质被乱用了,政治上的宽容、讲道理的态度、该让步时就让步,还有看长远的眼光,这些都慢慢没了,原来的坚持和执着也变成了倔脾气和一意孤行。
一年多之后,时间来到了公元1086年,也就是宋哲宗在位的头一年元祐元年。那时候,66岁的王安石在四月离世,而68岁的司马光则在九月也走了。
到了公元1093年,也就是宋哲宗在位的第八年元祐八年,宣仁太后带头,花了九年的时间,把新变法给废除掉,恢复了以前的老规矩。到这时候,赞成变法的人就被叫做“元丰党人”,而反对变法的人则被叫做“元祐党人”。
这一年,宋哲宗开始自己掌管朝政,他又把元丰党人重新任用起来,并且全面恢复了之前的新政变法。
在章惇这位宰相的带领下,元祐党人受到了严重打压,整个过程持续了六年多。苏轼等元祐党人,包括他们昔日的友人章惇,对他们变得非常苛刻,导致他们晚年过得非常凄惨。
从章惇的做法中,大家这才清楚,什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尽全力对付政治对手,以及政治迫害和政治暗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甚至公开说要挖出司马光的坟墓鞭打尸体,还打算出一整套折磨元祐党人及其子孙后代的办法。不过,当另一个元丰党人提醒他这样做会惹来无穷无尽的报复后,他才不情愿地打消了这个狠毒的想法。
公元1100年的时候,24岁的宋哲宗去世了,然后宋徽宗赵佶就当上了皇帝。向太后不喜欢之前的新政策,所以她来主持朝政。向太后又把那些元祐党人找了回来,把新政策给取消了。
元丰时期的那些官员也受到了毫不留情且非常狠毒的惩处。
这时候,北宋朝廷里主要是排挤异己、打击不同政见的人。过了九个月,向太后因病不再管朝政,宋徽宗就开始亲自掌权了。可没多久,政局又开始动荡不安……
结尾的话:
赵佶当了皇帝后,其实没啥治理国家的好办法。刚开始掌权那会儿,他还挺能接纳别人的不同看法。他给全国发了通知,说自己对元祐、元丰的事不计较,只看对国家好不好。

可没想到,才一年多时间,赵佶那“不靠谱”的性子就露出来了。他先是把曾布、蔡京这些元丰党人给提拔了上来,然后又突然来了个大转弯,说话不算话。特别是蔡京掌权后,整个帝国的官场都被他搞得越来越没脸没皮,低俗下作了。
蔡京刚当上官的第二天,徽宗就颁发了一道命令,说要废除元祐年间那些政策。打那以后,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的打压保守派的“元祐奸党案”就开始了,还立了“元祐党人碑”。
蔡京给皇帝送上了一份被认为是“元祐奸党”的名单,上面列着好几百个当时很有名望的人,像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程颐、黄庭坚、范纯仁等,他们都是文化上大有成就的人物。
和章惇想要挖司马光的坟鞭他的尸那种粗鲁暴力相比,蔡京的手段更为阴险狡诈。他专门挑那些政敌们最看重的东西下手:一生的名声和后代子孙的颜面。
他把名单传到了全国各地,要求所有的州、府、县、郡都必须把“奸党”的名字刻在石碑上。这些“奸党”的后代不能留在京城,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更不能和皇族结亲……这个命令影响特别大,以至于现在有些地方还能看到刻着“元祐党籍”的石碑。
蔡京现在打击的不只是那些政治观点不同的人,他还把政敌、和他抢位置的人、看法不一样的人,以及以前批评过、得罪过他的人都列进了奸党的名单。这里面还有他以前的同伙,像章惇和曾布这样的人。

接着,那位画画特别棒,审美也超一流的皇帝宋徽宗,就用他短短的一生,去追求那些无穷无尽、高雅至极的乐趣了……
到现在,咱们该明白点啥了吧?一个帝国的倒塌,可不是哪个人或者哪个大事情就能搞定的。从尝试改革那会儿起,就已经给国家的灭亡悄悄铺路了,不过话说回来,国家最后没了,跟改不改那法子本身,关系还真不是特别大。
再强大的王朝也承受不住这样一次次的折腾和变故。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好像老天爷故意跟北宋王朝过不去,短短几年里,每经历一次动荡,王朝的精气神和实力就削弱一点,最后变得无可救药。
大宋那种光明磊落的气度,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离世后,就慢慢不见了。他们打下的基础,却被那些不争气的接班人越搞越糟,一路滑坡。
苏轼和范纯仁悄悄离开之后,一个时代就正式落幕了。跟他们一起远去的,不只是那个曾经灿烂辉煌的朝代……
说说岳飞被害的真相,到底是谁下的狠手害了岳飞
从真实历史的视角来看《大明王朝·1566》里的几个关键角色
说说司马迁的不足之处——读《史记》,聊聊李广、卫青和霍去病
一千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搞错了关羽——说说襄樊之战的来龙去脉。
千秋岁月似飞鸟,独留一羽在云霄。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